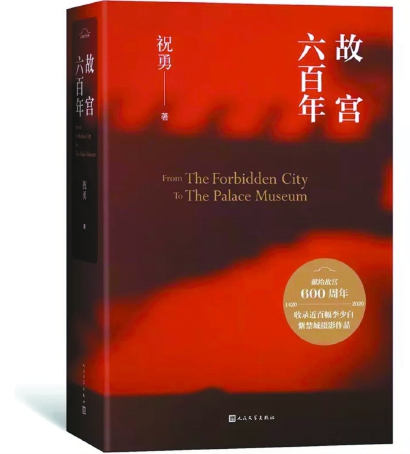
《故宮六百年》祝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回望故宮目光要超越六百年
我必須穿越層層疊疊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來。我不想沉重,我想輕靈,想自由,像從故宮的天際線上劃過的飛鳥
讀書周刊:從2014年開始動筆,《故宮六百年》寫了將近5年,可謂是個大工程。您曾說,寫紫禁城與建紫禁城在有些地方極為相似,具體來說有哪些相似之處?
祝勇:這本書我寫了5年,但真正集中寫作是三年半左右,跟建紫禁城的時間基本一樣。當然人家說紫禁城那么大一個工程都建完了,你只是寫一本書。但是紫禁城是多少萬人同時在建,而這本書完全是我一個人,一邊寫一邊查資料。它同樣需要耐心,需要經驗,更需要時間,可以說我是用文字重溫了一次紫禁城建成的過程。
讀書周刊:除了《故宮六百年》,您對故宮的書寫可以構成一個大系列——《紙上的故宮》《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故宮的古物之美》都是近年的暢銷之作。您想通過文字,讓讀者看到怎樣的故宮?
祝勇:故宮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王朝政治意義上的故宮;一個是文化意義上的故宮。現在不管是書籍還是影視劇,比較多的是從王朝政治意義上去觀察故宮。這是一個視角,但是遠遠不夠,因為這里除了故宮還是博物院。
故宮里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有陰陽、五行,回望故宮,目光要超過六百年,因為它是五千年的精華,非常多元并豐富。我出的《故宮六百年》,也超越了六百年,比如1420年朱棣為什么建成故宮?為什么要在北京定都?不管你怎么講,六百年都裝不下這些。
現在的故宮博物院有186萬件文物,從陶器、玉器,一直到當代的作品,體現了中華文明是沒有斷流的文化,這從故宮里是能找到物證的。
我寫了這么多關于故宮的書,著眼的都是文化意義上的故宮。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寫的《在故宮尋找蘇東坡》,大家會很奇怪,蘇東坡是宋代的,為什么要在故宮尋找他?實際上,故宮收藏了蘇東坡的墨稿、他的一些書法作品,還有與他同時代的歐陽修、黃庭堅的作品。今年秋天,故宮也要舉辦蘇東坡大展,所以從文化意義上去挖掘故宮的內涵非常重要。
讀書周刊:很多人認為,您寫故宮的最大特點,是用文學的方式來描述它。
祝勇:確實,我的寫作風格偏向文學,不過我雖然用文學的寫法,但都從真實的史料出發,不存在演繹和想象。此外,我書中的細節特別多,我希望能真實地體現人物的性格和歷史的狀態。
紫禁城夠大,六百年太長。面對這座凝結著時間和空間的歷史之城,走進這座容納了無數的人與事的故宮,人的話語容易顯得無力,乃至失語。一個人的生命丟進去,轉眼就沒了蹤影,我必須穿越層層疊疊的史料,才有可能把它找回來。我不想沉重,我想輕靈,想自由,像從故宮的天際線上劃過的飛鳥。
我一直認為故宮這些文明的遺物是有感情的,有生命力的,過去的文物都凝結了當時人的情感,對生命的寄托和塑造。就比如蘇東坡寫《寒食帖》,1082年的寒食節,蘇軾前途未卜,窮困潦倒,被貶官第三年了。蘇東坡那一天肯定很傷心,很自責,很無助。想寫兩首詩,拿起筆,寫下了這個帖,這就是他情感的迸發。所以我看這些文物首先不是看它們在歷史上的意義或從審美角度去評價,而是關注創作者的情感,和與他們能產生的交流,這種交流是可以跨時空的。文物是載體,能夠實現我們和古人的對話,這是我寫這么多年故宮,我的最初用意和最想表達的。
讀書周刊:這樣的對話就是我們了解過去和現在、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那把不可或缺的鑰匙。
祝勇:寫歷史就是要了解中國人的內心和中國歷史的本質,我覺得比較好的歷史書寫是要深入淺出,有很淺的層面,生動好讀;也有深的層面,有作者自己的思考。中國人寫歷史,以《二十四史》為代表,還是有自己的價值觀在里面的,不是純粹地寫歷史,實際上就沒有純粹的客觀歷史,這背后還是有個人的判斷。這些判斷和我們當下的價值觀都是有關聯的、相銜接的。
每個人物都試圖影響他所處的時代,尤其是這個宮殿里的掌權者,他們希望能夠引領他們的時代,同時他們也被那個時代所控制。我們也是將來的歷史人物,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里說了一句話,“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在這樣一個參照系里,它會為我們文明的走向提供一些參照。
是物質的城也是人群的城
紫禁城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城,是物質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個社會,是世界的模型,是整個世界的縮影
讀書周刊:2002年,您到故宮工作前就寫完了《舊宮殿》,從那時寫到現在,寫了故宮18年。在您看來,故宮意味著什么?
祝勇:其實,我也總在想,故宮到底是什么?歷史學家、建筑學家給出的所有定義,都不足以解釋它的迷幻與神奇。在我看來,紫禁城是那么神奇的一個場域,是現實空間,卻又帶有神異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宮,或者命運交叉的城堡。因為它的內部,人影憧憧,魑魅交替,有多少故事,在這個空間里發酵、交織、轉向。
讀書周刊:您曾說,紫禁城有墻,但紫禁城又是沒有邊際的。
祝勇:簡單說,紫禁城就是一座城。它的外圍有城墻,在它的內部,有辦公場所(三大殿、養心殿等),有家屬宿舍(東西六宮等),有宗教設施(梵華樓等),有水利工程(內金水河等),有圖書館(昭仁殿等),有學校(上書房等),有醫院(太醫院等),有工廠(造辦處等),有花園(御花園等),除了沒有市場,紫禁城幾乎包含了一座城的所有要素。但紫禁城里又是有市場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個大市場,忠誠、信仰、仁義、道德,都可以標價出賣,這些交易在這座城里一刻也未停止。
在這個物質空間里,也容納著各色人等,包括皇帝、后妃、太監、文臣、武士、醫生、老師(皇帝及皇子的講官)、廚師、匠人等等,他們在各種建筑中生存和相遇,合縱連橫,沆瀣一氣,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應運而生。紫禁城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城,是物質的城,也是人群的城。它是一個社會,是世界的模型,是整個世界的縮影。
紫禁城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一個生命體,猶如一株老樹,自種子落地那一刻起,它就沒有停止過生長。
所有的事物都涵蓋了故宮是寫不完的
故宮里面這種文化的氣脈特別養人,它在養你,無形之中就會形成故宮人自己內心的修養和外在的氣質
讀書周刊:用文字書寫故宮,是否也讓您重新認識了故宮?
祝勇:最初,在我心里,封建帝制是非人性的,故宮又是封建帝制的大本營,因此在這座城里,每一個人都受著非人性的戕害,甚至連皇帝本人都不例外。所以,我寫的《舊宮殿》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書,充滿了殘酷和暴力。而這種戕害的最大犧牲品,就是太監。一個孩子閹割進宮,這個孩子進宮那一天,剛好是宣統皇帝退位那一天,中國從此不再有皇帝。我寫的這個孩子的身上,凝聚了太多人的命運。
但通過無數次走進故宮、體悟故宮,再到后來的書寫故宮,我發現,我的認知在發生奇妙變化,故宮不只是封建帝制的大本營,它的內涵是豐富的,它凝聚了我們民族對美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耳濡目染都是歷代的藝術家、能工巧匠們嘔心瀝血做出來的精品,雖然隔著幾百年的時光見不到他們本人,但這些東西會不知不覺把它的精氣神注入你的內心。故宮里面這種文化的氣脈特別養人,它在養你,無形之中就會形成故宮人自己內心的修養和外在的氣質。
讀書周刊:你多年來一直在寫故宮,情感上的動力是什么?
祝勇:我特別喜歡故宮,我就想深入地了解它,不想只有一知半解,然而知道得越多,就發現自己知道得越少,你只能不斷地再去了解,好像是一個遠行者,已經完全為當下的景物所著迷了。可能走得太遠,就忘了自己當時為什么要出發了。
其實我有這樣的想法——有朝一日寫至少一部兩部跟故宮沒關系的東西,但是到目前為止,我想寫的關于故宮的書還沒寫完,還有進一步想說的東西,其他都顧不上。我倒不擔心這個范圍太狹窄,因為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里,從中國到外國,所有的事物故宮里面都涵蓋了,所以我覺得故宮是寫不完的。
讀書周刊:故宮里的現代人,也是您在《故宮六百年》中經常提到的,這些人如何影響了您?
祝勇:他們身上有特別令我感佩的東西。比如,我寫到了莊嚴先生,他瘦小枯干,手無縛雞之力,在抗戰時期為了保存故宮文物,帶著故宮文物南遷,他和老院長馬衡先生,最關注的文物之一就是那十件石鼓。石鼓非常重,一個就有一兩噸重,但它很有象征性,這就是他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在那樣一個戰亂的國破家亡的時代,他們的責任就是保護古物。
故宮有動起來、活起來的一面,也有靜的一面。我們的專家、學者、修復師們,擇一事,終一生,他們的心是那樣的沉靜,紅墻外的喧囂好像都與他們無關,這是故宮最令我感動的地方。
來源:解放日報 | 王 一 2020年10月10日07:12